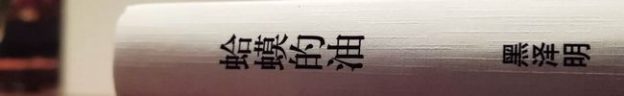疫情继续发展。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前天全国确诊883例(其中贵州确诊3例),疑似1073例,死亡26例;今天确诊2018例(其中贵州确诊5例),疑似2684例,死亡56例。确诊人数两天就翻番,两天新增超过1000例,已经开始大爆发。目前全国23个省、5个自治区、4个直辖市、2个特别行政区,只有西藏还没有“沦陷”(或许是因为地广人稀,信息传递不及时)。昨天,包括贵州省在内的全国30个省、市、区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最高级别的一级响应,贵阳市暂停了一切文化、宗教、聚餐活动,开放日期另行通知。
17年前的非典,病毒比这一次的还要凶猛,从1人传播到1000人的时间是4个月;这次的病毒肺炎,从1人传播到1000人的时间大概是20天左右。疫情爆发点的武汉,政府从开始的瞒报、不作为,到仓促封城,从公共信息看不到武汉在后勤、医疗物资储备和救治的应急工作,省级医院缺乏物资竟然不得不在网上对外界求助,第一时间响应和参与的竟然只有民间组织。整个湖北,尤其是武汉,这次疫情表现出来的是一种无政府状态,政府和官员的表现让人极度失望。
17年前的非典时,我在深圳。每天自我隔离在家,百无聊赖就不管年代、不管黑白彩色、不管中外,在网上一部接一部看电影。现在每周看电影的习惯就养成在那时。现在记得那段时间新接触到的四个日本人:黑泽明、北野武、山田洋次和藤泽周平,可见我年轻时知识和眼界的贫乏和狭隘。
非典时看了黑泽明导演的《姿三四郎》(1943)、《罗生门》(1950)、《七武士》(1954)、《蜘蛛巢城》(1957)、《用心棒》(1961)、《影武者》(1980)、《乱》(1985);北野武自导自演的《座头市》(2003)开启了我的北野武观影线,并一直延续到《极恶非道3》(2017)也还没有抵达终点;山田洋次从《黄昏的清兵卫》(2002)开始,延续了《隐剑鬼爪》(2004)和《武士的一分》(2006)。这三部电影,都改编自藤泽周平的小说,由此开启了我的藤泽周平阅读线。现在书架上有《黄昏的清兵卫》《蝉时雨》《隐剑孤影抄》《隐剑秋风抄》《秘太刀马骨》《三屋清左卫门残日录》和《小说周边》等七本藤泽周平作品集。
可以说,非典那段自我隔离的时间,无意间塑造了我现在的观影和阅读习惯,从而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昨晚到今天继续宅家读书,看了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和程耳的短篇小说集《罗曼蒂克消亡史》。
林怀秋译井上靖《杨贵妃传》,是腊月二十八那天,在万东桥花鸟市场旧书摊淘到的,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1版1印。这个译本语句不清顺,看了10页放弃了。例如:第一页“寿王瑁是玄宗与三千后宫中最宠爱的武惠妃之间所生的皇子”,“之间”两字是语病,应删掉;第四页“被置于过去不曾想过的新的命运之中”,如果拿掉后一个“的”,为“被置于过去不曾想过的新命运之中”就更顺畅;还有第八页“御汤的宽绰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砌起来的,浴槽的边缘雕着鱼、龙、雁等的浮雕”句,也是语病。“鱼、龙、雁等的浮雕”的“等”字后面应该跟随的是一个界定雕刻内容和范畴的词,如“动物”;并且如果拿掉两个“的”,将这句改为“御汤宽绰的浴槽是用白玉石砌起来的,浴槽边缘雕着鱼、龙、雁等动物的浮雕”,读起来就顺畅很多。但如果要达到清顺,还需要语句上付出更多的功夫。一直认为老一辈人文人译书,是讲求“信达雅”的,现在看来,也不尽然。我一直相信,母语的修养,决定了第二、第三语言的最高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