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下半年的一天,在网上买书看到有个买满多少减多少的优惠,于是把收藏夹里《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加进了付款清单。这两本当初放进收藏夹时只是匆匆看了书名,以为是正好又和工作多少有点关联的工具书。
正月初四,大雾阴冷不宜野出,备好了纸笔,安顿好了娃,正襟危坐在桌前翻开,野?《行动的书:关于策展写作》咋个是艺术评论文集嘞?不是策展写作闷?挖哦!这酸爽,就像之前买《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为是和《学箭悟禅录》(现译名《弓与禅》)那样,充满了禅趣的摩托车修理手册;而《他者的历史: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制作》,对我这个人类学和历史学的伪爱好者来说,完全无法把各篇章之间联系起来。不过终于还是有收获——哪怕只是谈资而已——真正的历史人类学需要构建一个兼顾时间与空间的框架:“人类学的岛屿”这一提法凸显了传统人类学研究在社会空间上的界限性,从共时性的角度研究作为整体的某个地方社会;而历史学则更多关注不同世界在时间维度中的存在状态与变迁过程;二者的结合则正因为“历史是社会在时间中的开展,而‘社会’则是历史事件的制度形式”。
简单看书名买书还是太冒险了。我的问题就在于,说得太多,做得太少;想得太多,读书太少。
他者的历史
“历史在变化中发生,或许也只存在于变化之时刻。历史首先是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同时,历史不止是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连串事件,而且是从我们身上开始倒叙的话语构造,是一种不断自我回溯和自我解释的行动。而现在,历史成了专家们操持的文本工具,成了现成知识,成了意识形态的操作对象,成了无数新闻、旧闻与轶事的集合,成了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以至于我们要去一再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
贵州城文工业遗产博物馆的小伙伴们正在进行中的“贵州工业口述史”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追问公共历史与私人历史的关系,反复搜寻口述历史与人民记忆的踪迹”。截止到2015春节前我们的最后一个工作日(2015年2月14日),博物馆的小伙伴们在博物馆各位顾问的指导和带领下(这个不是客套话),历时一年多,完成了超过130位深度参与贵州工业史中各种人物,整理出来将超过400万字和近300小时的口述记录。这只是一个开始——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尝试。如果能完成第1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在试着做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如果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那时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
之所以觉得要完成了第5000位口述记录,才可以说做了一点关于“贵州工业口述史”的事情,是因为我们认为,历史不应该只有宏大叙事下的一个(唯一)版本,也不应该被各种意识形态固化。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历史事件之中所有人的历史,而不总是被升华、提炼、萃取的“历史”。如果一个事件有5000人参与和卷入其中,那关于这个事件的表述,就不会只有唯一的一个声音;每一个事件中人,都有自己的一个关于这件事的发展脉络和结果,都有自己在这件事里的体温和记忆,而不能被抹掉或总被一句“高度浓缩”的标语或“定性的结论”所覆盖。由那么多人一起身处其中、持续发生、变异着的一个接着一个事件,那经过个人之生命测度过的事件之流,那真实存在的无数小历史的鸣响与嘈杂的和声,怎么可能是与个体生命无关的东西?
一个事件如果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就必须或曾经被认为是重要的。即历史的构成和记忆的选择都不是强迫性的追溯既往,和文化叙述一样,过去的故事也是事件真实结果的选择性记述。在某种意义上,“口述历史”便是建立在对民众记忆的有效性的相对承认上,承认人类同时是历史的主体和客体。那么,历史的真相,可能是没有真相,也可能是有无数个真相,也可能是无数个真相所构成的群体意识的“真相”。而这个“口述历史”的行动本身,也已在重现、构建、参与和组成新的“历史”。因为就算我们如人类学家所要求的那样客观,但人毕竟不是机器,人类学家也必然是参与(Participant)观察者,参与——并修正(无论多么微小)——我们正在调查和理解的对象——观察者永远是他或她所观察到的变化中的情景的关键部分(Leach 1989:39)。
现在看到的,和这个博客里过去10年来的各种哼哼唧唧,都可看作由我自己进行的自己的“私人历史”,我既是“我”的主体,也是“我”的客体,同时呈现为并行的“我们的历史”和“他者的历史”——“他者”的范围,也包括数目庞大的个别历史(separate histories)。所以“并行”,是因为“他者”不应该是被牵扯进“我们的历史”才被历史所承认,而是“他们”一直以来都有与“我们的历史”无关的历史。
关于“乡土”的想象
文化和历史是互相容受的(adjective)(Hastrup 1985:246),而不是实质上分离的两个实体。
现在,全球建立起一个客体化的自然和根据“领土”来区分的民族空间,这是一种地理上的暴力行为,通过它,世界上每个空间都受到勘测,都被画入地图受到控制。通过这种全球性的绘图行为,本地生活变成了展示,地方性日常经验成为文化资源,无数人群成为被注视的表演者。
由于缺乏足够的当地历史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缺乏必要的亲熟性的“本土经验”,文化性解读甚至人类学知识基础上的解读就沦为了寻找、辨识文化符号和身份印记的“征候式阅读”,甚至成为一种别具针对性的误读(“分享异国风情”在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文化误读的合法性),似乎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外在的观测眼光,“文化”的概念才得以展露容颜。
在真实生活中,象征意义或文化设计与物质情况间并不是因果关系,概念实存与物质实存是同时存在的。身着传统服装、娴熟地搬弄本地民俗和政治符号,这并不是自我身份的确认——相反,这恰是认同危机的佐证,其实质是试图赢得认可。在可以看到的设法通过传统的重建以提高村民的自我意识时,看上去的那些试图想达成传统的重建的活动,正设法“使他们再变成他们从来也不曾是的样子”。因此,这样的解读、阅读和误读,只是种种关于“乡土”的想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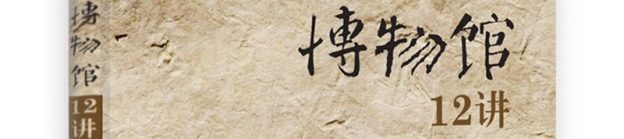
 【街头摄影】贵阳2015年3月3日
【街头摄影】贵阳2015年3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