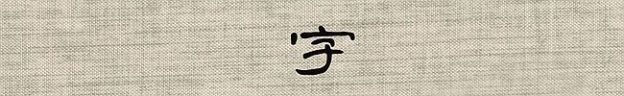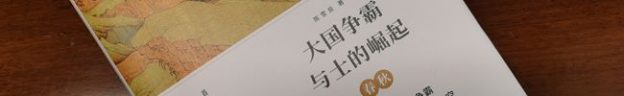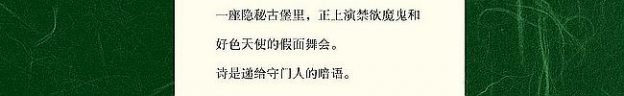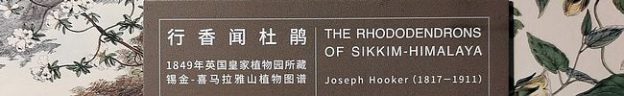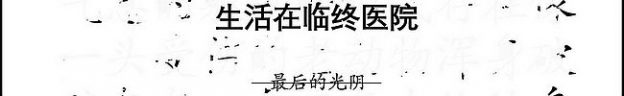《十三行小字中央》,收江弱水六年里的二十二篇“既不算‘随笔’或‘散文’,也不算‘小品’的文章,因为从造句到谋篇,既不随便,也不散漫,反而很多算是‘大品’。”小品也好,大品也罢,于我而言,都是“千钧重量的微言一克”,大有收获。随手录几段以作读后纪念:
1、所谓“十三行”,是晋王献之所书曹植《洛神赋》,残帖仅存十三行,共二百五十字,故名。这十三行小字历来被认为是“小楷极则”,在书法史上地位极高。它有两个传本,晋麻笺本和唐硬黄纸本。唐硬黄纸本上有柳公权的两行题跋,被认为是他临写的本子。晋麻笺本北宋时儒内府,徽宗曾刻石,拓赐近臣。靖康之后,这麻笺本及其刻石的下落,众说纷纭。(《十三行小字中央:朱彝尊的风怀诗案》)
2、黄侃自嘲学问“屑微已甚”,杨树达自号“积微”。训诂学家从不废话一吨,总是微言一克,但这一克微言却是从偌大的古籍库中一本一本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细读下来再精炼出来的,这就有了千钧的重量,动它不得。(《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3、郭在贻《释“努力”》一文,令人称绝。古诗《行行重行行》:“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努力”一词,各选本均不加注,显然认为是“用力”“勉力”的习惯用法,“努力加餐饭”就是劝君能多吃点就多吃点。但郭氏说,除此义之外,自汉魏到隋唐,“努力”还有“保重”“自爱”的意思。《三国志》卷九裴松之注引《魏末传》,有“好善为之”与“努力自爱”对应的话。郭氏还举了杜甫《别赞上人》为例证。(《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4、柳永《望海潮》写杭州“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我们多半也想当然地认为,“参差”是形容房屋密集却又高低不齐的样子,但郭在贻说“参差”是唐宋诗人习见的俗语词,含义颇为复杂,但这里应该训为“大约”,是说杭州当时有大约十万户人家。(《微言一克的重量:从郭在贻的训诂谈杜甫诗的校注》)
5、要说外语是打望世界的窗,方言便是安顿灵魂的床。只会说普通话的人,怎么看都像个塑胶人,来历不明,去向可疑。而方言给人底气,指向你生长的那一方水土。所以,四川话里头有花椒味,山东话里头有大蒜味,陕西话里头有臊子味,闽南话里头有蚵仔味。(《栀子花茉莉花》)
6、文学的诗意是怎么失去的?可以说,自从文学找到了意义,就失去了诗意。要怪文学研究缺乏诗意,首先得怪文学缺乏诗意……我们都清楚,给一篇文章归纳段落大意和中心思想,初中生都干得来。而能够敏感文心,细查文脉,没有的精微的体会和辨识是不可能的。此所以现在研究文学,有个中等资质就够了,而有诗意的文学研究,非才智之士莫办……赏析其实是一种珍稀的能力,是一切批评研究的入门,也是极文章之壸奥的不二法门。没有高人指点,你就是捧着作品一字一字的读,也无由窥见其室家之好、宗庙之美……身心整个儿沉浸在作品的世界中,手触摸到文本的机理,与作者同呼吸,象忧亦忧,象喜亦喜,情绪被裹挟进去,而每每又跳脱出来,为你一一指证其得失所在,真是快意而过瘾。总之,文学研究需要敏感、洞察,以及最重要的热情。对你的研究对象,你得爱,或者恨,也许是惋惜。(《文学研究中的诗意》)
7、中国传统诗学的好处是精辟,缺点在空疏;西方诗学则以分析见长,而有繁琐之弊。这两种阐释模式,各自利病鲜明,合则双美。(《顾随先生的讲堂》)
江弱水《十三行小字中央》,浙江大学出版社2020年4月1版1印。总阅读量1526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