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经有一刻,当英国和中国因两种花木——罂粟和山茶——兵戎相见时,世界版图以两株植物的名字重新划分。
罂粟果实经加工提炼制成的鸦片,在18-19世纪的东亚作为麻醉毒品被广泛使用。鸦片的种植和加工均在印度——这片由诸多王公国家组成的次大陆,于1757年臣服在大不列颠的王旗之下。在英帝国的庇护下,印度鸦片的经销由东印度公司全权负责。
山茶叶经采摘加工可冲泡饮用,通称为茶。一直以来,中华帝国几乎完全垄断了这种“清澄碧玉”的所有产销环节:种植、采摘、加工、炒制及其他加工方式、批发、出口……一切一切,皆由此一国独享。
近二百年来,东印度公司向中国出售鸦片并以所获利润购入茶叶;而中国反过来用在茶叶贸易中获得的白银,从印度的英国商人手中购买鸦片。
鸦片——茶叶贸易对于英国而言不仅仅是获利那么简单,它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中不可取代的重要元素。英国政府每10英镑的税收中,就有1英镑来自茶叶的进口与销售,平均每个英国人每年要消费一磅茶叶。茶税被用于铁路和公路建设、公务员薪水支出以及一个蒸蒸日上的工业国家方方面面的需要。鸦片对于英国经济而言同样重要,它为印度——这颗维多利亚女王皇冠上闪耀的宝石——的经营管理提供了资金支持。尽管政府一直以来都希望印度能够在经济上自给自足,但19世纪中叶英国在印度西北边境发动的一系列扩张战争,却将它从这块富饶而辽阔的次大陆上所能获得的利益迅速消耗殆尽。植物商品的三角贸易是此时推动世界经济运转的原动力,帝国的车轮随作物的生长、加工与销售而转动:大不列颠从印度鸦片和中国茶叶中均分得一杯羹。
19世纪中叶的中英外交是一部不幸的悲剧。北京城内高高在上、贵为天子的皇帝于1729年下诏“严禁”在中国销售鸦片,然而持续了数十年的走私仍使鸦片得以流入(值得注意的是,不列颠诸岛的鸦片贸易亦遭维多利亚女王禁止,然而她的法令却得到了广泛服从)。鸦片销量迅速而稳定地增长着,从1822年到1837年,销量增加了5倍。终于,在1839年,统领广州港的宫廷大臣(钦差大臣林则徐——译者注)为这些外国人的目无法纪以及民众吸食鸦片上瘾后的病态所激怒,扣押了夷馆区内的所有外国人,并要求以300名英国人手中价值600万美元(约折合今日的1亿4500万美元)的鸦片为赎金。当鸦片贩子们被迫妥协、人质获得释放之后,这位大人命令500名中国劳力对将近300万磅的毒品用盐和石灰加以搅拌,将混合物倒入珠江。作为回应,年轻的维多利亚派皇家海军出战,以武力使获利丰厚的鸦片——茶叶贸易得以延续。
在战争中,英国一举打垮中国,清政府粗劣不堪的木制帆船根本不是女王陛下以蒸汽为动力的现代海军的对手。作为和平条约(实为不平等条约——译者注)的一部分,英国人赢得了经一个世纪的外交恳请而不得,以至于无人再抱希望的对华特权:香港岛,外加大陆五处新通商口岸,或是说贸易港口。
自马可·波罗时代起,鲜有西方人得以窥探中国内陆地区。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0余年间,英国船只被限制停泊于广州,一个珠江口贸易城市的港口。英国人无法光明正大地涉足所居货栈以外的场所,许多人甚至从未见过离商馆区仅200多码远的、25英尺高20英尺厚的广州城墙。而现在,挟战争胜利之威,中国的内地终于向大英帝国开放了一条缝隙——仅限贸易。
《南京条约》签订、五口通商后,英国商人做起了美梦:堆积在中国内地的华贵丝绸、精美瓷器以及喷香茶叶正等着被他们销售到广阔的世界。商人们开始构思一种可能:绕过难缠的中间人和控制广州货栈的商行直接与中国的生产商打交道。银行家则在幻想着无以计数的财富、矿藏资源、粮食谷物、经济作物以及梦寐以求的开花植物——一个遍地都是待装载商品的巨大国度。
然而,通过第一次鸦片战争所建立起的新秩序并不稳固。在英国坚船利炮的压力下签订的无法忍受的条约,令中国这一曾经骄傲自满的国度蒙受了彻底的羞辱。英国的政客与商人们担忧受辱的中国皇帝可能借鸦片本土生产合法化颠覆由协议建立起来的脆弱平衡,进而打破印度(也就是不列颠对罂粟种植的垄断。
伦敦方面现在坚持着一种意见:应该且必须保障对英格兰的茶叶供应。距鸦片战争爆发、拿破仑战争结束已有相当长的时间了,然而那些曾奋战在特拉法尔加(Trafalgar)和滑铁卢(Waterloo)的勇士们却依然强势左右着英国的外交政策与舆论。亨利·哈丁(HenryHardinge),一位曾追随纳尔逊勋爵与威灵顿公爵,协助他们战胜拿破仑的名将,在担任印度总督期间,曾针对目中无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危机做出如下警告:依我看来,北京政府完全有可能在几年内将中国的鸦片种植合法化,这里的土地已被证明像印度一样适宜这种作物的生长,可能导致(英国)政府目前主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之一彻底枯竭,基于这种推断,我认为最理想的对策是尽可能地鼓励在印度进行茶叶种植。依我之见,后者(在印度种茶)从长远来看很可能为国家提供同等收益,并且是比当下鸦片的垄断销售更加保险的财政来源。假若中国真的将鸦片合法化了,那么在三角经济上将留下一个非常致命的缺口:英国将再无资金进口茶叶、支付印度战场的军费或承担本土的公共建设项目。中国的鸦片种植业将为两大帝国耻辱性的经贸依存或“由两种花木交易包办的不幸婚姻”画上句号,这种“离异”是大英帝国所承受不起的。
印度境内的喜马拉雅山脉南麓与中国最好的产茶地几无二致。除坐拥喜马拉雅山的高海拔和肥沃土地之外,云山雾罩的环境使茶树在享受露水滋润的同时又遮蔽了骄阳烈日。经常的霜冻气候更为冲泡出的茶水增添一份醇香浓厚,令其口感更加丰富、浓郁、可口。
随着植物商品贸易顶破东亚贸易的资产报表,它们对于世界格局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研究它们的人们——曾经被大众视作区区花匠之流的人——摇身一变以植物学家的身份受到众人瞩目。到了19世纪中叶,植物学家已不再被视为戴着工作帽,穿着钉靴,躬身伺候着他们的鳞茎、花卉和灌木的体力劳动者,而是以勇敢的冒险家与世界的改变者闻名。他们采集各种对英格兰乃至帝国各地具有科学、经济与农业潜在价值的异国植物。移植成活植物群的新技术也发展得更为先进,使职业植物猎人们得以采集、运输越来越多的异国植物样本。
不再受限于中国最南端的沿海口岸,如今英国得以深入到茶叶的种植与加工区域。但若要茶叶产业成功落户印度,英国需要从最好的茶树上采集最健康的样本、成千上万的茶种以及中国顶尖茶匠传承了千百年的工艺。完成这个任务的人必须是一个植物猎人、一个园艺学家、一个窃贼、一个间谍。
这个担负着大英帝国希望之人,名为罗伯特·福钧。
——《茶叶大盗:改变世界史的中国茶》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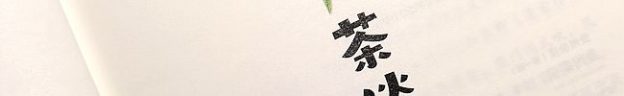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古称赵州。唐代从谂禅师(778年~897年)曾住锡赵州观音院,弘法传禅达40年,人称“赵州古佛”,有“吃茶去”、“庭前柏树子”等几桩有名的禅门公案。
河北省石家庄市赵县古称赵州。唐代从谂禅师(778年~897年)曾住锡赵州观音院,弘法传禅达40年,人称“赵州古佛”,有“吃茶去”、“庭前柏树子”等几桩有名的禅门公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