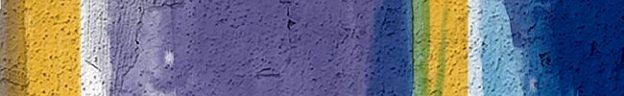哲学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不过可以有一个非常抽象的回答,所谓哲学就是爱智慧。要注意的是,这里的爱,指的并不是宗教意义上的无私的爱,更不是出于本能的感性冲动及浪漫情怀的情爱,而是温和而理性的“友爱”。所以说,在对待智慧的时候,哲学家不像男欢女爱的狂热,也不像宗教情感的博大无私,它是一种彼此尊重和欣赏、温和且理性的热爱。这种爱不以占有为目的,而是以相互激励共同进步为目的。这也意味着哲学作为爱智慧之学,从来不会妄自尊大地认为占有了智慧,哲学家只是一个以温和而理性的方式热爱智慧的人,一旦有人宣称自己占有了智慧,这样的人要么就是先知,要么就是骗子。
哲学的思考从来都无法换来掷地有声的物质回馈,甚至都无法在这里找到“2+2=4”那样板上钉钉、笃定无疑的知识。那我们从哲学这里指望什么呢?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括,那就是“打开!”——打开你的视野,打开你的既定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让你从一种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用一种充满怀疑的、审视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因为,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才是最有意味和最让人着迷的问题。
周濂《正义的可能》,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87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