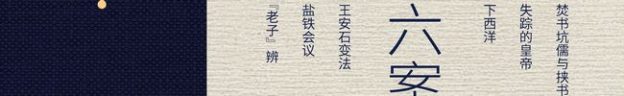老子,既是人名也是书名,而无论其人其书,俱皆成疑。
自《史记》首立传,老子之存在已疑点遍布。其姓氏虽云“李氏”,然“春秋二百四十年间无姓李者”,李是晚出于战国的姓氏。至于“名耳,字聃”,后人谓“名耳之说始自汉代……先秦典籍中皆称老子或老聃,没有一处称‘李耳’”,有关“聃”,钱穆先生认为,照《说文》之释来推想,“其实‘老聃’只是寿者的通称”。
二千多年来,五千言思想面目已极模糊。顾颉刚先生的古史“被层累地造成”说,用于《老子》最为贴切。而《老子》到底是一本什么书,真相勘破,竟然一直要等到清末——
严复在其1905年所作《<老子>评语》中说:“夫甘食美服,安居乐俗,邻国相望,鸡犬相闻,民老死不相往来,如是之世,正孟德斯鸠《法意》篇中所指为民主之真相也。世有善读二书者,必将以我为知言矣。呜呼!老子者,民主之治之所用也。”
颜渊问政,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礼已失,于是孔子欲以“仁”复之,岂不恰是应了“大道废,有仁义”一语?时有贤者往见孔子,出而叹道:“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者,“施政教时所振,以警众者也。”可见儒以仁义礼智信救世,正乃“六亲不和,有慈孝;国家昏乱,有忠臣”之验。就实质论,老子愤世与孔子救世对于现实的体认是一致的,并不矛盾。所不同者,孔子欲以救世者,老子断然认为不能救。在此,老子显出了思想的跳脱性,非但不信仁义智慧可以抑暴制暴,而且站在更远的前端,预言各种漂亮辞藻将化作假仁假义,反过来骗世害民。而历史果然证明“智慧出,有大伪”的警示入木三分,其情形代代不绝、愈演愈烈,甚至儒家纲常本身后亦不逃此命运。“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真正质疑的是,社会究竟是把自己托付于那些救赎,还是使之置诸压根儿无须其匡扶之地?
陈柱先生1927年感叹说:“呜呼!老子之学,盖一极端自由平等之学也!”《老子》一书“蒙昧两千余岁,得严氏而后发其真”,“故知《道德经》是言治之书”。严复此语当属两千余年来有关五千言的最重要论断。二千余年无人能道而严复言于1905年,确是时代使然。帝制时代,老子所言“治”,盖如鸡同鸭讲,终淹没于种种误读曲解。
昨夜读完李洁非《古史六案》的第六案《<老子>辩》,新知大长,也解了我前读《太平广记》老子一篇的惑。在宋代编就的《太平广记》里,老子既不“名耳”也不“字聃”,而是“老子者,名重耳,字伯阳”,因“其母感大流星而有娠,虽受气天然,见于李家,犹以李为姓”又“母怀之七十二年乃生,生时,剖母左腋而出。生而白首,故谓之老子。”关于老子到底是谁,“或云,上三皇时为玄中法师,下三皇时为金阙帝君,伏羲时为郁华子,神农时为九灵老子,祝融时为广寿子,黄帝时为广成子,颛顼时为赤精子,帝喾时为禄图子,尧时为务成子,舜时为尹寿子,夏禹时为真行子,殷汤时为锡则子,文王时为文邑先生。”又“一云,守藏史。”这还不算完,又“或云,在越为范蠡,在齐为鸱夷子,在吴为陶朱公。皆见于群书,不出神仙正经。未可据也。”这个正儿八经的玄幻要点在最后四字“未可据也”。难怪位于全书第一卷第一位,也是五十五卷“神仙传”中的第一位神仙。
与《太平广记》中老子的玄幻相比,七年级中国历史教材中言之凿凿说:“老子姓李名耳”前面也应加上“或云”二字才行,否则与《太平广记》何异?
李洁非《古史六案》,人民文学出版社2020年10月1版1印,硬面精装,18.7万字用了五天才粗粗读完,总阅读量第1305本。《古史六案》是真正学者的学问之书,史料充足,有辩有析,抽丝剥茧,步步为营,有温故,有新知,值得二刷,甚至多刷,但感觉对文言文只是初高中语文教材那点底子的阅读者来说,门槛还是有点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自身的文言文基础不够好的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