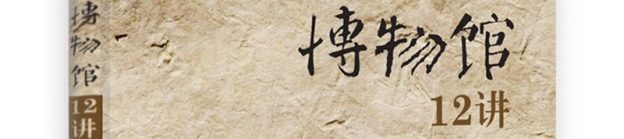我做事热得慢,遇事反应慢,在当机立断眼疾手快上,差太座太远。昨天在微信里抢购书券,我一无所获,而太座斩获乐转城市书房六百元和二十四书香书店一百元共七百元购书抵扣券。不服不行。
“下周你生日。”太座提醒。
“哈!正好,当我生日礼物。”没有比书更适合的礼物了。
今天早餐后,背上背包进城“血洗”两个书店,共洗来书二十本,我的十六本,女儿四本。
乐转城市书房十种十四本:
唐浩明《杨度》上中下三册,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七年一月一版一印,一四九一页,一百五十二万字,定价九十九元。从清末到民初,杨度十七岁中秀才,十八岁中举人,精通法学。他参与过公车上书,是满清四品官员;和康有为、梁启超、黄兴是好友,跟汪精卫、蔡锷、齐白石是同学,怂恿袁世凯称帝,赞同孙中山共和。营救过李大钊,是杜月笙的师爷,入过佛门,加入过国民党,最终加入共产党。买这套书,想了解下一个人到底是怎么将一个人生活成十八种。
唐德刚《李宗仁回忆录》上下册,“中国近代口述史学会从书”之一种,架上唐德刚作品第五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零一五年二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印,七百九十八页,六十六万字,定价一百四十九元。李宗仁寓居美国期间,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在“东亚研究所•中国口述历史学部”襄赞下,于一九五八年开始自述三十余年的戎马生涯及所参与的军国大事,由历史学者唐德刚整理撰写,遂成《李宗仁回忆录》。
白先勇散文集《八千里路云和月》,中国友谊出版公司二零一九年十月一版一印。特别赠送白先勇签名版藏书票和台湾书法家董阳孜手书条幅。我架上有《台北人》,这是白先勇的第二种,应该不错。
张宏杰散文集《历史的局外人:在文学与历史之间游荡》,东方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一版一印。张宏杰的书,架上已有并看过《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坐天下》《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这是第四种。
鄢敬新《尚古说印》,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四月一版一印。应该是一本印章和钤印入门书。反感书店将书塑封,无法探知内容,又不好意思在书店里摸出手机搜这本书,我觉得这是对纸质书的亵渎,所以就只好根据封面封底设计来盲测。内容怎么样,读过才知道。
《贫穷的本质:我们为什么摆脱不了贫穷》,二零一九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印]阿比吉特·班纳吉和[法]埃斯特·迪弗洛合作完成。这本书是我今天采购书单上唯一店里有的书。中信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九月二版,二零一九年十二月十四印。买这书的目的,就在书名——我想变成有钱人,是什么阻止了我成为一个有钱人?今天在书店,我对太座说,虽然我们没有钱,但也不算贫穷,现在我真正感到缺乏的不是金钱,是时间,每天用来读的时间还是太少。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江西人民出版社二零一八年二月一版一印。关于一种新的伦理学——土地伦理学——人只是大地共同体的一个成员,而不是土地的统治者,我们需要尊重土地。据说与《瓦尔登湖》《寂静的春天》并誉为自然文学三部曲,这下三部曲齐聚,《瓦尔登湖》读过,然后就是去继续读书。
维罗妮卡·亨利《夜莺书店》,北京联合出版公司二零一七年五月一版一印,一部关于书店的小说,我猜;妮娜·乔治《小小巴黎书店》,中信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二零一八年四月一印,一本煽情的关于书的畅销书,也许;费莉希蒂·海斯-麦科伊《世界尽头的图书馆》,百花洲文艺出版社二零一七年八月一版一印,借书和图书馆为道具和场景的治愈系小说,大概吧。
谷崎润一郎《春琴抄》,青岛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七月一版一印,“青鸟文库”口袋本之一种,凑单的。
二十四书香书店两种两本,虽少但是今日淘书最佳:
黄裳《古籍稿抄本经眼录:来燕榭书跋题记》,中华书局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一版一印。黄裳是当代著名藏书家,学问渊博,文笔雅健,所撰藏书题跋尤见功力,为文献研究者和收藏爱好者所重视。这本书是我架上黄裳第六种,可作为我“野外自学”版本学周边资料收藏。
黎庶昌《丁亥入都纪程》,朝华出版社二零一九年一月一版一印,竖排繁体,“清末民初文献丛刊”之一种。据清光绪二十年(1894)“光绪甲午秋日刊于川东道署”刊本影印,无句读。光绪甲午即中日甲午战争那年。原书作于清光绪十三年丁亥,贵州遵义人、郑珍的学生黎庶昌因母去世告假返乡期满后赴京待命时。全书采取日记体的形式,详细记录了作者由黔取道四川、陕西、山西入都(北京)途中的见闻与感悟。其间他不仅考察了所经地区的民生实业,还对许多重点形胜的地理文化做了详细描述和考证,纠正了《读史方舆纪要》《水经注》《蜀輶日记》和《汉书·地理志》等古籍中的一些错误,不仅是一部文笔清新雅致的学人游记,也是一部资料翔实、考证精准的地学游记。架上贵州人民出版社“贵州古近代日记丛刊”第五辑录有日记四种,《丁亥入都纪程》其一,横排简体,不如这个版本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