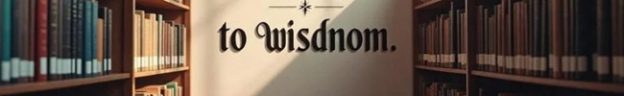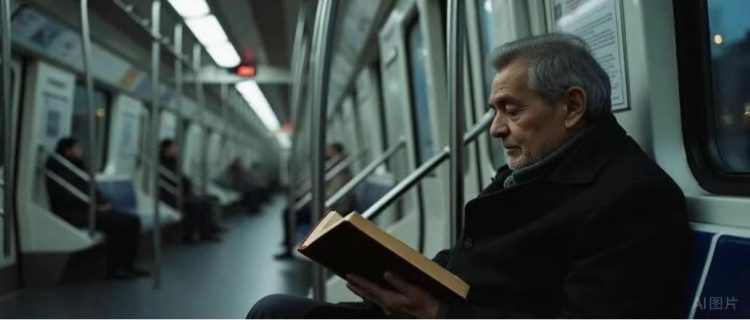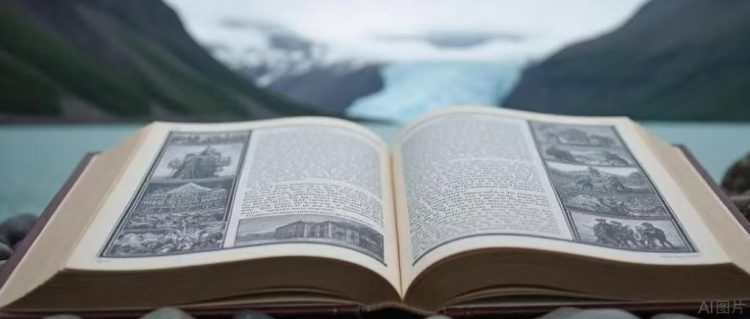到北欧上学,除了英语,还有“母语”B1的等级要求。例如丹麦要求丹麦语,挪威要求挪威语,反正不管怎样都要再学一门外语,Isaac确定了芬兰是唯一的目标。
这个挑战非常大。尤其对Isaac的自我管理能力和学习能力要求非常高。
我们根据时间和目标,为芬兰语、英语、数学、中文(部分学校可选此作为“第二外语”)和历史这五门必修课排了权重。
Isaac将历史排在了第一,语言第二,兴趣爱好的足球排在了第三,数学保持每天少量时间的持续学习和家庭教育就绰绰有余,中文保持阅读写作和讨论就很好。
在这个学习计划中,每天耗时最多的不是权重第一的历史,而是语言。英语和芬兰语的学习时间Isaac保持在每天5小时左右。
历史的学习,本周结束《基督教欧洲的巨变:1517-1648》63万余字的共读学习,Isaac也完成了万余字的相关阅读笔记。
我们每两个月为一个学段,一个学段“攻克”一个阶段性目标。这来源于芬兰教育的启发。芬兰打破了传统的两学期制,把每个学年分为5-6个学段,每个学段包括6-7个星期。学段制使学生在本学段内的课程设置相对集中,便于对所学课程的完整掌握。同时,这么做也有利于教师集中精力,在相对较短的时期内将某一课程讲授得比较透彻。
新的学段从5月1日至6月30日,除开节假日,八周时间。
新学段分量最重的英语和芬兰语学习,将继续保持;历史将根据Isaac的兴趣点,进入三十年战争(1618-1648),欧洲历史上最为惨烈和复杂的战争之一。这场战争不仅是神圣罗马帝国内部的宗教冲突,更演变成了全欧洲范围内的权力斗争和利益争夺。它的影响深远,导致数百万人的死亡,改变了欧洲的政治格局,并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Isaac选的共读书是彼得·威尔逊的《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这部83万字,903页的“历史教材”,单就阅读量来说就不轻松。并且还必须放在神圣罗马帝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新教与天主教冲突的框架下去读,而这种种概念也显然不在中国读者的舒适圈内。新学段“开啃”对象就是它了。
新知,Isaac带我认识了华伦斯坦——在“三十年战争”中,与新教阵营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并称双雄的神圣罗马帝国统帅。
加时,我们给了里昂与曼联的加时赛。20年没看球的我,场上的球员一个也不认识,Isaac一一介绍,抢断的是谁,射门的是谁;我们这一对年龄相差30岁的“男孩”(男人至死是少年嘛)饥肠辘辘对着电脑屏幕点评锋线没有大作为,后卫的破门和门将的第六感……今天第十多次我拍着他的肩膀说,两年以后,去现场看球吧!
Isaac,两年以后,去欧冠决赛现场看球吧!
也闲书局没有彼得·威尔逊《三十年战争史:欧洲的悲剧》,离开时买了冈仓天心“东方三书”之一的《理想之书》,四川文艺出版2017年2月1版1印。
今天是第三十个世界读书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