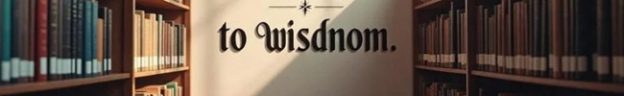Isaac带来了周末整理的目标大学和专业介绍,以及报考要求。我们讨论分析后,根据这些要求对四月的内容做了调整。
大卫•科尔比的《芬兰史》,不知道是原文如此还是译文佶屈聱牙,差不多四分之一的句子要读两三遍才大致明白,徒增阅读难度但又找不到更好的版本。约翰·亨·伍里宁的《芬兰史》,武汉大学译本在1973年后就没有再版。与Isaac讨论下来,无论如何还是先跑一遍再说。另,欧洲史的进度也要加快,一个月要完成50万字的阅读、资料查询和笔记整理。50万字,如果是写得不错,文字顺畅的小说,不过是两三天的阅读量;但如果是专业学者撰写的严谨学术著作,挑战就很大。
我们能够找到的关于芬兰的资料如此有限,或许未来你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我说。1917年独立,这么年轻的国家,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时间里,从贫穷落后一跃而成世界上的高度发达国家,它做对了什么?看世界人均年阅读量排行榜,会发现一个规律,发达国家的人均年阅读量基本上都高于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是因为国家发达、收入高、生活悠闲幸福指数高了所以读书的人多了?还是因为读书的人多,书也读得多,所以成为国家发展的动力之一?还是有更多更复杂的原因?
“我猜是因为教育。”Isaac说。
“我们对誉为‘世界最好’的芬兰教育充满了好奇,国内各个社交媒体上对芬兰教育的各种分析也褒贬不一,并且似乎都有可靠的来源,如果你去到那里,进入其中,或许会有较直观和准确的判断。不论国家还是文明,从历史发展和互相欣赏的角度,而不是简单去做孰优孰劣的比较,会发现更多,收获更多。”
今天的对谈,还涉及到“乌合之众”与独立思考,人是否一定要合群以及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什么等。他的同龄人在学校里为了掌握一个知识点在重复刷题,我们在学校外讨论关于教育有多少种可能性,如果人生和教育真的有“起跑线”的话,父母的认知就是一个家庭的起跑线和天花板。我还是那个观点,人与人最大的不同,就是认知的不同。认知不是学历不是知识,而是智识。没有智识,一个人拥有再高的学历也只不过是一个知识的容器。说到这个容器,AI已经超越了所有人,再去以学历或占有知识的多寡来作为受教育程度的标准,毫无意义。
我倒是见过一些行走的知识容器,大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