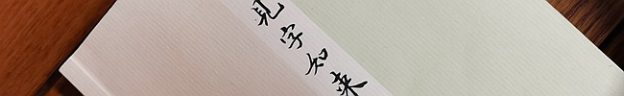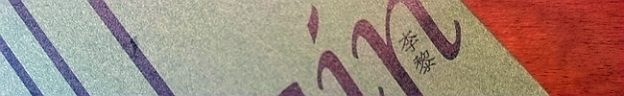前天,2025年的最后一天,晚餐是例行的家庭聚会。乘地铁从2号线起点中兴站到3号线顺海站,有20个站,车程近1个小时。平时空荡荡车厢只有我一个人的“豪华包车”,难得的挤满了人,一半是背着书包的小学生和拉着拉杆箱的中学生。
我在不开的那一侧门边,把背包放在两只脚中间地上,从包里抽出张大春的《見字如來》,靠在门边二刷。第一次读这本书,大概是在五年前,具体内容都忘了。“咦?这个字……好像认识,又好像不认识。”旁边座位上,一位穿着蓝白相间校服,背着书包,看起来大概小学四五年级模样的女娃娃,歪着头,看着我手里书的封面,似在自言自语,又好像在和我说话。
“这个是‘你看见我,我也看见你’的‘见’字。”我说。
“那第四个呢?”
“是‘你从哪里来’的‘来’字。”
“‘见字如来’?什么意思?”她问。
“就是见到这个字,就好像来了。”
“哦。”她转回过头去,靠在椅子上,“看见的见字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真是好奇怪。还有那个‘来’字,也是又像又不像。”这次她是真的在自言自语,没再问见到这个字就什么来了,我也就不说了。就这么站着看了几站,手酸,换了一只手拿书,撇了一眼旁边座位,不知道女娃娃在哪站下的车。想起我在她这个年龄,家里没什么书可看,翻来翻去就是上中下一套三册《水浒传》,简体字都还认不全就开始半认半猜看繁体字。那一套《水浒传》是我阅读和认字(繁体字)的启蒙,现在还记得一套书都被人用一种三角形的尖锐物刺穿,纸张又脆又薄,不小心就会翻烂。现在回想起来,那套书应该是那段历史的物证。可惜,后来被一位大我十几岁的堂哥借去,就没再还回来。
现在的小孩子,都不认识繁体字,就更不知道,因为考试不考所以也不想知道一个字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后面有什么历史和故事了。好可惜。不过还好,并不是所有的华人地区都只学简体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