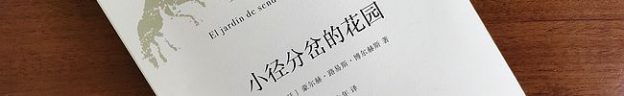从住的这里去省城贵阳或县城龙里,距离几乎是相等的。搬来三个星期,脱离了省城,但还没去看看县城是个什么样。早起赶路十几公里,想从一份有特色的早餐开始了解这个县城。临出发在书架上抽了两个版本的Lonely Planet《贵州》想看看关于龙里的介绍,但只和临近的贵定县合并在一起提及两个景点,没有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也就是说,这个县城,和全省其它的87个县城一样普通,甚至更为普通,普通到乏善可陈。
进城,果然。花了半小时,吃了一份在任何一个贵州小城都能吃到的早餐,在步行街买了一份贵阳“但家香酥鸭”,去逛了县城最大的书店——只有两个临街门脸,一半是教辅和文具的新华文渊超市,花卷挑了两本青春小说,还算开心,因为新给她买的南派三叔《盗墓笔记·十年》和《沙海》两天下来就还差最后一章就看完了。我选了《在城崎:志贺直哉短篇小说集》。三本结算共139.8元。我的这本书,可买可不买,但逛书店不能只是让娃买书要求娃读书,自己也要有所行动和表率。
下午,或许是午睡起来昏昏沉沉,理解不了博尔赫斯深邃的思想,博尔赫斯全集之一,《小径分岔的花园》里七篇小说,我竟没有一篇能顺畅读超过三页。就连著名的《小径分岔的花园》也是毫无感觉,每一个字都认识但不知道好在哪里。于是放弃,但好歹读过了,就得记录一笔。这次在书名页没有写“读毕”,而是写了“不知所云”。在《铁币》和《七夜》之后,我确定不喜欢博尔赫斯,对此我毫不讳言,就像读不懂也不愿意再读《尤利西斯》和《追忆似水年华》一样。甚至连书摘都懒得做。阅读首先是为了取悦自己。
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博尔赫斯全集之一,王永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6月1版,2023年6月第27印。总阅读量第147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