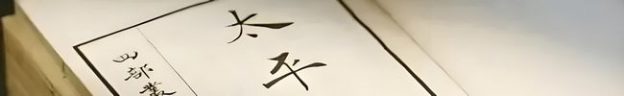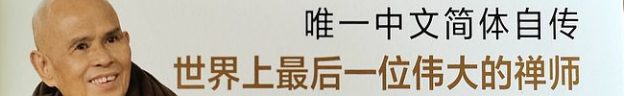1896年留着大胡子的奥匈帝国犹太记者西奥多·赫茨尔写了一本小书《犹太国》,印数寥寥三千册。然而这本书象征着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
二战后,许多从纳粹大屠杀下幸存的下来的犹太人前往祖先的巴勒斯坦,并陆续组建了几大军事组织。以当时议会反对党领袖梅纳赫姆·贝京领导的“伊尔贡”(意为“民族军队”),因领导人大多身受纳粹之害,多行事偏激;开国总理本-古里安领导的“哈加纳”(意为“防卫”)一派最为强大,行事风格也相对稳健。
伊尔贡和哈加纳又合作也有矛盾,甚至一度差点兵戎相见,但他们在关键时刻又能团结一致,贝京坚持“犹太人永远不能内战”,解散伊尔贡,以个人身份加入哈加纳,这才有了今天的以色列国防军。
长约五十米、高约十八米的哭墙,是近两千年前犹太王国宫殿被罗马人拆毁后剩下的最后一段遗迹。犹太人世世代代的最大愿望,莫过于回到这堵墙下痛哭一场。如今梦想成真,犹太人收回了哭墙,却发现这个世界依然没有安全可言。
冯翔的《奔袭》,围绕1976年7月3日“恩德培行动”展开。在我看来,这本书的副标题(如果需要借此对内容做一个概要说明的话)也可以叫“恩德培行动始末”,或“内塔尼亚胡家族的崛起”,或“以色列现代国家历史上最美好的一天”。
书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不是以色列突击部队飞越三千五百公里,从乌干达首都恩德培机场成功解救出一百多名人质的英勇;也不是行动间接导致乌干达第三任总统“吃人恶魔”阿明的垮台,而是在面对分歧时,以“永远的反对党领袖”贝京为代表的色列人的态度:
这不是政府和反对党之间的党派之争,这是一个最高级别的全国性问题。我们——反对党将支持政府为拯救犹太人的生命而做出的任何决定。不管我们之间有什么分歧,不管我们对各不相同的信仰持多么坚定的态度,不管我们之间的争论有多么刺耳喧嚣——依照议会民主制度,所有持不同政见者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来表达意见。在专制的风暴中,我们需要这样的民主来克服障碍,通过考验;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将越来越强大。
欲言又止,言尽于此,多说无益。
冯翔《奔袭》新星出版社2023年11月1版,2024年1月2印,签名本,购于也闲书局。总阅读量第1504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