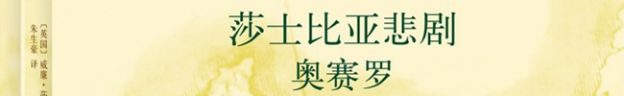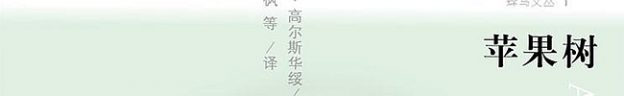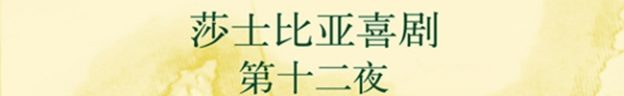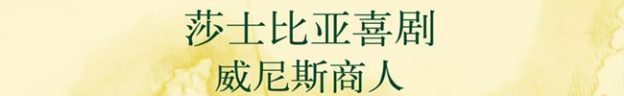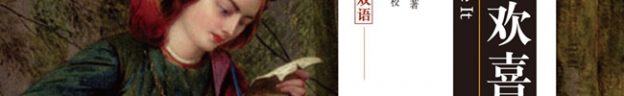莎士比亚似乎钟情于女扮男装。在《皆大欢喜》中长公爵的女儿罗瑟琳女扮男装并化名为盖尼米德,身为罗瑟琳时即收获了老罗兰爵士的儿子奥兰多的爱,盖尼米德又获得了牧女菲比的爱。在《威尼斯商人》中富家女鲍西亚女扮男装化身律师,打赢了爱人巴萨尼奥的挚友安东尼奥与犹太人夏洛特的官司,救了安东尼奥的命,同时收获了爱情和友情。
《威尼斯商人》这部戏里有浓厚的对犹太人的种族歧视,但读下来最精彩的部分也是犹太人夏洛特在威尼斯法庭上,面对来自威尼斯公爵、巴萨尼奥、葛莱西安诺等所有人的道德绑架,坚决要求按照执行的,一个人与一个时代的抗争。
这个抗争源于基督徒,同时也一样是威尼斯商人的安东尼奥以自己还在途中的商船上的货物和自己的信誉为担保,向犹太商人夏洛特借了三千块钱,以资助自己的朋友巴萨尼奥去向鲍西亚求婚。夏洛克为了缓解基督徒对犹太人的误解并希望“交个朋友”,愿意不收利息,只象征性的约定到期若无法偿还,“就得随我的意思,在您身上的任何部分割下一磅白肉,作为处罚。”安东尼奥认为“很好,就这么办吧;我愿意签下这么一张约,还要对人家说这个犹太人的心肠倒不坏呢。”
可谁知道,安东尼奥的船失事,到期无法偿还这笔借款。这时,安东尼奥和巴萨尼奥的朋友萨拉里诺对夏洛克说:“我相信要是他不能按约偿还借款,你一定不会要他的肉的;那有什么用处呢?”
夏洛克说:拿来钓鱼也好;即使他的肉不中吃至少也可以出出我这一口气。他曾经羞辱过我,夺去我几十万块钱的生意,讥笑着我的亏蚀,挖苦着我的盈余,侮蔑我的民族,破坏我的买卖,离间我的朋友,煽动我的仇敌;他的理由是什么?只因为我是一个犹太人。难道犹太人没有眼睛吗?难道犹太人没有五官四肢、没有知觉、没有感情、没有血气吗?他不是吃着同样的食物,同样的武器可以伤害他,同样的医药可以疗治他,冬天同样会冷,夏天同样会热,就像一个基督徒一样吗?你们要是用刀剑刺我们,我们不是也会出血的吗?你们要是搔我们的痒,我们不是也会笑起来的吗?你们要是用毒药谋害我们,我们不是也会死的吗?那么要是你们欺侮了我们,我们难道不会复仇吗?要是在别的地方我们都跟你们一样,那么在这一点上也是彼此相同的。要是一个犹太人欺侮了一个基督徒,那基督徒怎样表现他的谦逊?报仇。要是一个基督徒欺侮了一个犹太人,那么照着基督徒的榜样,那犹太人应该怎样表现他的宽容?报仇。你们已经把残虐的手段教给我,我一定会照着你们的教训实行,而且还要加倍奉敬哩。
在威尼斯法庭上,威尼斯公爵希望夏洛克能够“放弃这一种处罚,而且受到良心上的感动,说不定还会豁免他一部分的欠款。”这实在是无稽之谈。所以夏洛克坚持按照约定来,否则公爵“就是蔑视宪章,我要到京城里去上告,要求撤销贵邦的特权。”读到这里,忍不住赞一声“干得漂亮!”
安东尼奥的朋友巴萨尼奥对夏洛克说:“你这冷酷无情的家伙,这样的回答可不能作为你残忍的辩解。”要求按照约定执行,竟然被说成是残忍和辩解。
巴萨尼奥提出双倍偿还,夏洛克不接受,“我只要照约处罚。”
公爵继续进行道德绑架:“你这样没有一点儿慈悲之心,将来怎么能够希望人家对你慈悲呢?”
我可爱的夏洛特说:“您要是拒绝了我,那么你们的法律根本就是骗人的东西!”
按说,夏洛克应该拿回自己的钱,并得到赔偿,以及来自众人的道歉,并赢得众人对犹太人的敬重。然而最终他却是这部喜剧中最悲惨的人,或者说其他人的欢喜都是建立在他的悲惨之上——
夏洛特改信基督教;自己的一半财产被借钱没还的安东尼奥接收,等他死后交给和自己女儿杰西卡私奔的罗兰佐;写下文契,声明自己死后全部财产传给女婿罗兰佐和女儿杰西卡。
夏洛特没了女儿,没了尊严,也没了财富,他的犹太人身份和他的财富,使他成了韭菜而被收割,即便他是正义的;而玩弄了法律和公正的人,就是女扮男装的,同时收获了爱情和友情的鲍西亚,以及她的爱人和朋友们。
所以,《威尼斯商人》会不会其实不是喜剧,而是悲剧?
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译林出版社2013年12月1版,2014年7月2印。2026年第14本,总阅读量第1629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