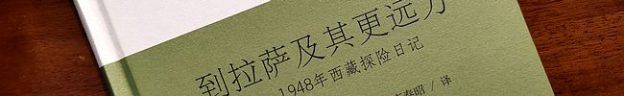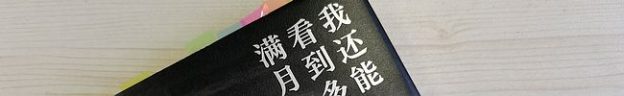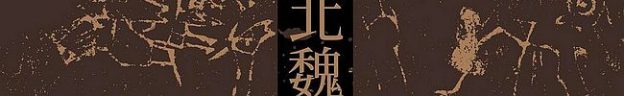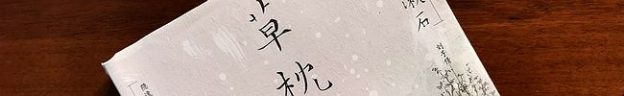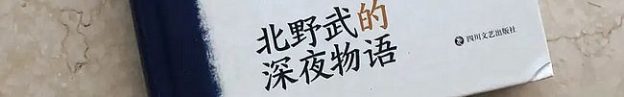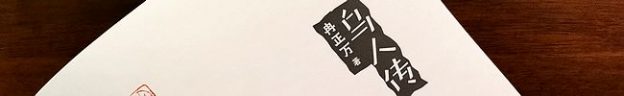“在西藏,对宗教的感受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它激荡着整个生命,控制着时间,在每个思想和每件作品中留下印记。”
“我一直认为人类的信仰是无形的、含蓄而现实的东西,它融于生命之中,却无法用手触摸。”
“科学的澄澈和它明晰的原理使我们神魂颠倒,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嘲笑缺乏科学依据的信仰,而自己却在被单一的思维所欺骗忘记了自己也正在迷信着什么——科学。我们傲慢的态度掩盖了一个事实——科学才是最嚣张的迷信。我们现代惯于外露的行为,已经把我们自己同内心世界发生的一切割裂开来,那是连接人类无知的现实和久远的过去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不安的恐惧和希望,还有不祥的预兆和断言。我们只有偶尔在梦中,才能现出那个世界的一丝朦胧曙光。对未知的恐惧驱赶着我们的思想重又跌回那令人不舒服的神秘世界里,但是我们的思想被推得越深它就一次次愤怒地欺骗性地弹回表面。它突然间汹涌而来,翻搅着,使我们宁静的感知变得模糊不清。”
“由于人的目的是多重性的,且存在冲突,因此人的行为有多种形式。人们被一个又一个的愿望驱使着,从来没有满足于自己的目的。不满足就像阴影一样伴随着人的行为。一次次新的愿望产生,一次次失望随之而来。冥想则是从外而内的反向路径,但这个过程是如此的艰难,很少有人能达到最深处的圣地。”
“任何一刻所产生的念头都会体现过去的经历和无限未来的一切可能性,是过去和未来的建造者,永不停息。”
“离开拉萨与离开其它任何一个城市不同。离开任何一个地方你都可以轻易地再回去,而拉萨却像是在世界之外,如此的遥不可及。离开拉萨犹如梦中的幻影消失,却不知它是否还会重现。”
作为佛教徒的图齐,在他的《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一书中,除了对科学与藏传佛教、内部世界与外部的物质追求有非常独到的看法,这还是一本很好的人文地理笔记。
例如对锡金的介绍,对西藏人物服饰的记录就非常精彩,堪为人文地理写作的范本。
[意] 朱塞佩·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是意大利著名东方学家,在藏学界、东方学界具有崇高的国际声望,他于1926年至1954年间先后在喜马拉雅西部地区、西藏等地进行了八次卓有成效的科研考察。《到拉萨及其更远方:1948年西藏探险日记》,是图齐第八次,也是最后一次进藏日记。中国藏学出版社2017年8月1版1印。总阅读量第1409本。我想把图齐的书的中文版都找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