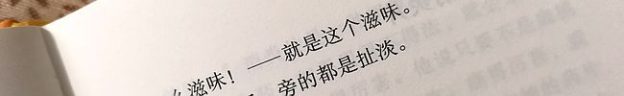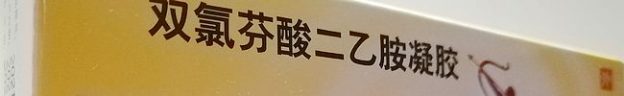今天的气温,从20℃降到6℃。正好上周讲到《随园诗话》,里面这一则就关于贵州的气候:
人但知商宝意先生以诗名海内,而不知其弟名书字响意者,亦诗人也。作贵州吏目,有《消夏吟》云:“雨后壑全响,日中崖半阴。壤檐蛛网结,嘉树雀巢深。永日无公事,闲居有道心。短衣随意着,凉意满衣襟。”又:“六月无三伏,一朝有四时。”“蜂巢当午闹,蚓壤趁凉歌。”真能写黔中风景。
“皂办处”微店里有客户下单,买了几十块钱的手工皂和防裂膏。下午去发货,路过小区里那个我认为适合开一个小书店的门面,看到开始装修了。是一家生活超市。招牌是那种“番茄炒蛋”的配色,大红的底上亮黄的字,让我想到村里会卖“粤利粤”“康帅傅”的乡村小卖部。在这条差不多五百米长的双向两车道社区街道上,这已经是第八家社区便利店,另外还有四家烧烤店、三家火锅店、两家卤味店、两家母婴店,以及洗衣店、五金店和若干空置门面。等我退休了,还是开一家地下车库书店兼老年活动室,没事就和走错路进来的人聊聊书,读读诗,喝喝茶,等死。运气好还能卖掉一本书或换来一杯米。
还是喜欢海豚出版社的精装书,做得真是好看。今天翻完上个月在也闲书局买到的董桥《小品:卷一》,海豚出版社二〇一三年四月一版一印,硬面精装,黄色仿皮烫金,还赠一张藏书票。这本集子,收的是一九七三年秋天到一九七四年初冬,董桥三十岁时在伦敦时写的东西。在开卷第一篇里,董桥也还算坦诚,“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东西实在写得不够好。”我读下来,也只能用里面《就是这个滋味!》一篇最后四个字来评价这本集子——“都是扯淡。”
我一直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或几个我,在各自过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前天,一位长年在外流浪的前同事发来一张照片,说在大理遇到一个开酒馆和客栈的老板和我很像,然后发来一张照片。看着照片,想:原来我就是长这个模样。昨天,这位老板加了我微信。他开酒馆,我却不能喝酒,滴酒不沾,我在他朋友圈推送的一份酒单下面留言:“我们是在互补还是体验完全不同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