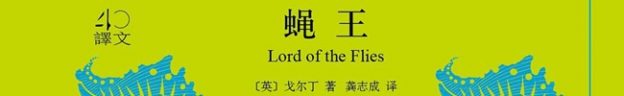下周三是“世界读书日”,今天把“四月之书”提到第一环节进行,各位学者分享自己正在读的书。我也分享了早上在地铁上刚读完的“法外狂徒张三故事集”,罗翔的《法治的细节》中两段——
“你希望别人怎么对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是普适的道德金律。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纯粹工具,无论为了保障何种社会利益,无辜个体的生命都不能被剥夺。
我们因为无知而读书,读书又让我们真正地承认自己的无知与浅薄。拒绝读书当然是一种愚蠢,但是因为读书而滋生出骄傲与傲慢是一种更大的愚蠢。
借此引出问题:在阅读这个过程中,什么是最重要的。
学者们说是感受、思考、收获,我说是时间,也即是自己的一段生命。生命是有限的,将这段时间用来读哪一本书,其实就是将这段生命托付给了哪一个作者,与他一起来共建自己的人生。所以阅读要保持,更要知道读什么和怎么读。
明天谷雨,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接着就进入夏天,选了清人曹尔堪的《谷雨后二日过镜槛小憩》作为诗词的开场。今天“花”字令结束,下周的飞花令就飞颜色了。一位中学生下午来“踢馆”顺便叙旧,进门第一句话就是豆总还有飞花令吗?她曾经最佳战绩是与十余人对战三十余轮,完胜。
对课,上联选了“几枝新叶萧萧竹”,上午高小班学者对出“数本旧书斑斑点”,由衷赞叹。窃以为,“数本旧书点点斑”更佳。有学者问毛豆你对的下联是什么,造化弄人,我准备了没人给我机会显一把,我没什么拿得出手的时候偏偏有人来问,“老实说,我觉得你们真的都很厉害,在短短三分钟就对出这么好的下联,而我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对出一个自认为拿得出手的。其实这上联是一首诗里一句,下一句是‘数笔横皴淡淡山’,作者是郑燮,也就是扬州八怪之一诗书画三绝的郑板桥。‘皴’是一种笔法,就是这样的。”我展示郑燮的《竹石图》,图上诗有两字与语文课本里这首诗的不同,到底谁才是正确的?感兴趣自己去了解一下吧。
上周讲谈有“苏格拉底的广场”讨论环节,今次没有讨论,有写作。上午高小班是世界各国文学奖获奖作品续写,各位学者人手随机抽取一部作品的一个片段,用时十分钟的未完成作品,悬念环环相扣,视角层层嵌套,我嘴上狠狠赞叹,心里暗暗可惜——如果能用更多时间来创作一个相对完整的作品,该多好。下午我选的是同一部作品的不同片段,学者分为两组合作创作,竟是两个与原作完全不同的故事。我在其中留了两个线索指向原作,是两个人名,一是卡西魔多,一是爱丝美拉达。“这些片段来自一部世界经典文学作品,我不论是说出书名还是作者名,你们都一定会发出‘原来是他/它’的感叹,语文课本里还收了这位作者的一封信。”
“不要卖关子,快说吧。”
“作者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书名是《巴黎圣母院》。”
“原来是这个啊!”
上午高小班,一人一句完成了主题七的《史记·周本纪》选段讲解。新来的学者在大家的鼓励下又蒙又猜出来的译文竟也七七八八,“毛豆这个时候就会说,‘小小《史记》不过如此’”有学者说。我说不错不错,我正要说的就是这句,小小《史记》,也不过如此嘛。我当然知道《史记》不会是这么容易的,但不论是文言文还是古诗词,三到六年级的学者更需要的不是标准答案,不是完全正确,而是不求甚解、不作过度解读,敢于去尝试,就算错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勇气,这样也才可能生出与古人对话而不是仰望的信心。对话是亲近的,平等的,而仰望既不亲近也不对等。
下午主题八“姜小白的逆袭:春秋的霸主们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和罗马城母狼”中,出自《左传》的《曹刿论战》本可以讲完,但我在鲁庄公说:“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处,说这里的“狱”不是监狱,而是指的诉讼案件,一下就飘了,飘到主张“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古希腊智者普罗泰戈拉那场让东西方法学界争论了千年的,著名的“半费之讼”。我承认,确实是有点“飘”了。
今次讲谈,居学三项任选,一是老规矩自选课题,二是续写未完成的故事,三是尝试完成《希腊简史》,一半的学者选了第二项,真好。
“毛豆,作业,我这次先小小写了个一千字,你看看。”一位六年级的学者把本子递给我,说:“我下次看看能不能八百字。”我接过本子,连声说好,“三句话讲不清楚的,三千字也讲不清楚;三句话讲得清楚的,三千字会讲得更清楚。字数不限,讲清楚为最佳哈。”
一天的讲谈结束,离开也闲书局时购书一本,戈尔丁《蝇王》。前两天莫名想二刷,在家里书架爬上爬下却怎么都找不到了。